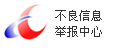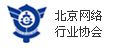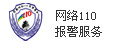简政放权为何成了一些人自肥的“花样”
据中国政府网披露,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严厉查处一些地方在简政放权中“玩花样”。“我听到反映,某个地方本来群众办一项手续需要到现场,交100元手续费。现在改革以后,人不用来了,直接发电子邮件,网上办理,但收费一下从100元涨到了500元。简直是匪夷所思!”总理说,“名义上说得很好听,‘不让群众跑断腿、磨破嘴’。结果呢?变本加厉多收钱!很多老百姓就说,咱宁愿多跑一趟,甚至多跑两三趟都行,车费也比这少得多呀!”
前两天,本报报道并评论了“公安机关不再开具18项证明”的新闻。乍一看该新闻,似乎令人点赞,认为这才是“方便百姓办事”,才是简政放权的应有之义;再一看,不对啊,公安局不开具这样的证明了,其他部门依然需要,公众咋办呢?现在要么到其他部门开,要么只能自己花钱开。对各种奇葩证明,公众的质疑和吐槽,不在于这些证明是在派出所、民政局还是在公证处开,而是觉得这些证明本就不应该存在!公安部门如此举措,显然算不上真正的简政放权。因此,在评论中,我们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政府部门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一切改革的目的,都应该立足于让民众方便,而不是让管理部门方便。
不过,什么才是“让民众方便”呢?这个问题显然并不简单。其中,除了涉及公共服务观念的转变,还关系到现实利益的考量。或者换句话说,公共服务观念转变之难,正在于种种现实利益的“阻力”太大。就新闻中李克强总理要求严厉查处一些地方在简政放权中“玩花样”的例子来说,通过改革,群众办手续只需网上办理,是不是更“方便”了呢?可以说是,但这种“方便”,却建立在相比以前多支付数倍费用的前提下。
这样一来,公众没有得到任何实惠,相关部门不用现场办公,事儿更少了,该收的钱却没少收甚至是“变本加厉多收”。如此简政放权的“花样”,问题出在了哪儿?
目前我们推动简政放权改革的逻辑,可以归于“限权”,而“限权”显然会充满利益博弈。包括新闻中李克强总理所举的例子,在简政放权中出现的种种“花样”说明,形式上的“简政”易,涉及真正“割肉”让利的“放权”恐怕就困难多了。比如,宿迁市市长王天琦便曾对媒体披露“简政放权”与地方职能部门的利益冲突:多数资格资质项目是部门依据自身职能、通过部门文件形式予以确立的,通过对这些项目的审批,不仅可拥有管理的权力,更有巨大的利益。“如气象局的防雷减灾气象技术服务收费,仅宿迁这样的普通地级市,2013年收费总额就达1064万元。”
在简政放权改革中,必然会触动相关行政部门的现实利益,引用我们另一位总理的话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回顾一下,近年来,实施“简政放权”改革针对的背景是什么?正是因为意识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权”与“利”结合得过于紧密。而“放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相关政府部门的非税收入锐减,也意味着一些权力部门人员自身权力寻租的空间缩小。因此,个别地方在简政放权中“玩花样”的过程中,一方面可能大张旗鼓地在服务程序上“简政”,另一方面却牢牢抓住原有权力和利益不放。
于是,在简政放权改革的利益博弈中,也就出现了简政而不放权,简政而不让利于民的情况。2014年8月31日新华社有一篇质疑“简政放权红利正在被谁吞噬?”的报道,其中披露,这两年,行政审批项目少了,但第三方中介评估事项近年却在不断增设。以前政府部门办理的很多项目,现在转移到了拥有政府背景的研究院所、检测机构甚至行业协会中。行政机关随便换个马甲就可以出来继续收费。湖北荆州一家化工公司准备上马一个新项目,项目投资100多万元。安监部门要求这家公司去当地一家中介做安全评价。公司负责人介绍,“安评”仅是指出不同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要求。“然后这个距离画几个框框,这就要20万。这还不包括验收,验收还要五六万。”政府部门不收费了,但指定的中介机构收费更厉害。以前政府部门机构收费200元钱能办完的,“简政放权”后反而2万元都难以办成了。
如何避免简政放权成为一些部门利益自肥的“花样”?首先可能还得回到简政放权改革的目的上来。简政放权改革,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办理效率、方便企业和民众,从而释放市场活力。那么,所谓简政放权,其实就是要让公共服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跑起来”,降低公众的办事成本,这个成本既是时间上的,也应该是金钱上的。“简政”,不应等同于服务上做“减法”,恰恰相反,而是要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做“加法”。“放权”,也不是把权力从“左手”转移到“右手”,而是实实在在地让利于社会、让利于公众。
来源:新文化报 由中华人物网编辑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