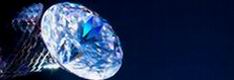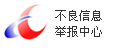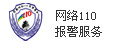重温迁徙路,父女二人寻根老屋解乡愁
重温迁徙路,父女二人寻根老屋解乡愁
“吾土吾乡”征文
◇ 冯举高 影子
导语
在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背景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许多人正经历着故乡被现代化浪潮席卷面临着消失的尴尬。他们前所未有地缅怀着乡愁,却又不得不面对无法回归的难题。
乡愁,何以安放?我们笔下的一对父女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
父亲冯举高用文字回忆那给人温暖的老屋,记录他永远抹不掉的乡愁情结。他笔下的老屋是深沉的,刻满了岁月走过的痕迹,保藏了他童年的记忆、诉说了温暖的亲情、提供了心灵的庇护,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季节交替、生老病死和酸甜苦辣。然而,老屋却随着岁月远去,父亲只能无奈惋惜……
父亲说,我们这些分散在四面八方的儿女,我们这些儿女们的儿女还能重回老屋么?父亲的殷切期盼在女儿这里得到了传承。对女儿影子而言,经历了多个城市的迁徙生活后,寻根是对故土最好的牵挂,于是,热爱文字和摄影的影子,用光影的方式寻根,在一次次的惊喜、意外、感慨、悲怆中,和自己的祖辈、老屋不期而遇。
父亲●回忆篇
母亲的老屋
文︱冯举高

我老家湖北保康两峪乡程岐村有一个地方叫双龙观。现在是“双龙观风景区”了。双龙观朝西的山下面有一个硕大的漏斗似的槽,也就是上头宽下头窄的一面大山坡,中间又向内凹进去一些。这个槽叫学屋槽。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为啥取这个地名。学屋槽中间凹进去的那一片是一坡梯田,田的中间有一堆乱石片东倒西歪直到如今。这就是我外公冯开级带着我母亲冯应青从南漳板桥陈家河逃荒到保康两峪程岐村后的第一个住处。
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可能是学屋槽属于阴坡,冬天几乎见不到太阳,又因为条件差,只能用石板砌房子,太寒冷的缘故,1941年外公带着母亲从学屋槽搬下来,到了一个叫楸树屋场的地方。楸树屋场相对于学屋槽来说海拔要低300多米,但还是在半山坡上。楸树屋场周边很敞亮,属于靠阳的一面,用母亲的话说,“屋场要比学屋槽好几百倍”。母亲没有读过书,这个倍数不知她是怎么比较出来的。1942年春,我父亲和母亲结婚了。当年母亲才19岁,因为母亲是独女,父亲就从南漳板桥张家倒插门进了冯家,名字也由张学传改为冯应祥了。父亲和母亲是按照老家当时当地的风俗拿八字对的亲。外公好赌,所以没有什么家产。女儿要结婚了,他才自己用山上的青㭎栎、黄栎桠子和野樱桃木等杂木架起三间茅草屋。母亲就是在这样一个柴屋里和穿着长布衫长得白白净净的父亲成的亲。
听母亲说,她在和父亲成婚之前,生了一场大病:出天花。这是要命的病,在当时的条件下,生这病的人十有八九都活不了。母亲说当时她脸上、身上、手上没有一块好肉了,全是天花流黄水,痂子掉一层又结一层,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已经被天花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外公痛苦,揪心地疼。他就这一个女儿啊。可病魔是残酷的,外公看着自己的女儿躺在屋里一角,他知道自己的女儿不行了,就去外村赊账买回一口棺材。母亲说那棺材就摆放在她的眼前,没有油漆,白森森的。
母亲已到了生命的尽头,她无可奈何地看着那口白森森的棺材突然想吃桃子了。我的老家最好的桃子也就是野山上长的毛桃子了,核桃大小。母亲张了张嘴,外公贴过脸去听自己女儿最后的声音。外公听出来自己的女儿想吃桃子。当时麦收刚过,正是毛桃子成熟的季节,外公拎起一个竹筐就奔向山野,两袋烟的功夫就提回一篮子新鲜的桃子。外公洗了后给自己女儿递过去。母亲吃了一个又一个,一连吃了九个桃子。第二天,母亲的精神好多了,竟然可以自己坐起来了,身上的黄水疱也渐渐地少了、小了。半个月后,天花不见了,母亲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外公高高兴兴地把还没有上漆的棺材卖了。可是母亲再也不想照镜子了,母亲青春漂亮的脸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小窝窝。读过私塾又很英俊的父亲并没有嫌弃母亲,他们如期举行了婚礼。1943年冬月初二,大姐冯举兰降临人间。
母亲说,大姐出生时是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外公家里穷得很,根本没有床,地上铺的苞谷杆子就是床,大姐就是母亲躺在苞谷杆子上生下来的。更糟糕的是六年后当母亲生下二哥冯举文时,不知哪里飞来的一把天火把外公用杂木架起来的老屋给烧的一干二净。外公仅有的一点资产也彻底没有了。好在当时正是土改时节,老屋坎上一户地主的房子建了一半,就近分给了我外公。这坎上建了一半的房子就是我记忆中的真正老屋了。而对于母亲来说,则是她从南漳板桥搬入保康程岐村后第三个老屋了。
这第三个老屋分前排后排,高两层。前排五大间,后排五小间,楼上楼下共10间,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房子了。但当时的外公家已经是一大家人了,那时我父母已生育了大姐和两个哥哥,外公带着母亲刚到学屋槽时,续了一个后外婆,后外婆带一个姓陶的儿子,比母亲小,我们管他叫小爹。后外婆又给外公生了一个女儿,我们叫孃孃(也就是姑姑)。常言道:树大分杈,家大分家。哪一年母亲和陶家小爹分的家,父母都没有给我们说过,但五大五小的房间是从正中间分开的,也就是说堂屋是各家一半。后来我记得堂屋的实际使用权都在我们这边。陶小爹把正屋门开到屋后面了,我们那里叫倒子屋。他们出门在东北角,我们家大门还是正南。
我的家虽然兄弟姐妹多,但就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一个就飞走一个。在兄弟姐妹九人中,我是唯一考学才走出重重大山离开老屋的。那是1980年深秋的一天,高考后通知书还没有收到。没有收到通知书父母就不让我下地干重活,担心我把身体累坏了学校不收我了,就让我在家做最轻的活。那一天,家里母猪快下小猪娃了,母亲让我守看着别让母猪把小猪娃压死了。那一天小雨和大雾把老屋和老屋周边的山山水水坡上坎下连同母猪栏都遮盖的严严实实。说实话,在我们那孤山野洼里一个人在家真还有点怕,好在我家还有一只狗陪我。那天它也很感兴趣,一直扒在猪圈上一个坎坎边,盯着猪圈不走,一会儿母猪开始下小猪娃了,一个两个三个……我正兴奋地数着,我弟弟从屋后面山上一边狂奔而下,一边高呼:“五哥,五哥,你的录取通知书来啦!”
这可是我整整一个夏天又加半个秋季的等待啊!苦苦的盼望终于有了结果。我顾不上数小猪娃了,跳上坎,迎着弟弟跑过去,一把抢过通知书,细看信封,上面写着“襄阳师专”,打开信封抽出通知书,才知道自己被襄阳师专录取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襄阳师专的概念,填志愿时也是老师帮助指点填的,反正我知道有了这张录取通知书就是跳出农门了,我高兴极了。可家里没有人祝贺,小弟弟也不太懂,我想到大姐家就在山坡上三里地外的地方,就拿着通知书从浓密雾中冲出去,大姐正好在家,她连声说好好好,就没有别的说了。我好失望,我想到保管室值班的父亲,就离开大姐家,飞快地往保管室方向跑去。到保管室要过一条深沟,一道山梁子才到,我平时胆子小,有雾天根本就不敢出门,那天有如神助一般,啥也不怕。见到父亲就把通知书递过去,父亲看了特别高兴,脸上露出慈爱幸福的笑容。我告诉父亲,家里母猪也下小猪娃了,走时已下三个,父亲说:“走,回家看看。”回到家,母猪已产下十二个小猪娃了,好在小猪娃都完好无损。“母猪下猪娃,越多越好,这是好兆头啊!”父亲显然因为我考上了大学而高兴。
老屋是用黄土干打垒垒起来的,顶上盖的是青灰色的瓦,顶上每一间房都有一到两块亮瓦。在老家那一带,家庭条件好的一间房可有三块到四块亮瓦,亮瓦越多,屋里就越亮堂,屋里越亮堂就说明这家里条件越好,条件差的人家一间房连一块亮瓦都没有,我家条件当时在村里是中等。
老屋有一间房有四块亮瓦,这就是后排靠西头的那间二楼 。这是我们家当时最好的房,当作客房在用。我最喜欢躲在这间房里看书了,看各种各样的书,包括父亲从一些地方捡回来的报纸。那时我们在老家是很少有小说杂志看的,遇到一张旧报纸能反复看数十遍,而小说一类的书多数都是借来的,这就需要抓紧时间不分昼夜的看了。白天,我帮母亲干活,只好偷偷地躲进这间小屋子里看书,母亲总是能很快找到我,让我去干活,我只好把书放下。夜里看又没有煤油灯,于是白天在山上干活时就顺便砍些松油多的树皮回来,夜里就点亮松油,第二天两鼻孔被熏的黑乎乎的,手指一抠像墨汁一般黑。
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在老屋地上滚过爬过,特别是小时候,父母照看不过来的时候,我们百分百的自由,我们想抓什么就抓什么,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包括黄土,包括鸡屎什么的。老人说这是搭地气,搭地气的孩子长大后病不多,身体好。
现在母亲的老屋孤零零的伫立在荒坡上,没有人看护,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后排二层楼已经不知在哪一个夜晚轰然而倒了,青灰色的瓦片,松木椽子和土墙上的泥混杂在一起;晒场上、门坎下、屋山头早已荆棘丛生,已经很难走进去了,看上去让我们好不心酸。
我时常在想:我们这些分散在四面八方的儿女,我们这些儿女们的儿女还能重回老屋么?还能在母亲的老屋住一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