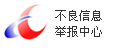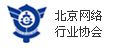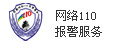独家专访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器官移植应不断创新
 石炳毅。(图片由解放军第309医院提供)
石炳毅。(图片由解放军第309医院提供)
主人公小传:
石炳毅,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等级2级。兼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肾脏移植专业学组组长、解放军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二十多个学术团体的重要职务。
以第一完成人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项,军队医疗成果奖一、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共4项。获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奖章,总后勤部优质服务先进个人、廉洁勤政先进个人、爱国奉献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
1996-1997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进修器官移植。长期从事泌尿外科与器官移植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近年来共开展心脏移植、双肺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亲属活体供肾肾移植等新业务、新技术30余项,均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解决了多项医学难题。
2011年何梁何利科技奖的获得者
新华军事:非常感谢石主任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听说您刚刚获得2011年何梁何利科技奖,首先恭喜您获此殊荣,您在科研与技术创新方面有哪些心得?
石炳毅:首先谢谢新华军事。我认为获奖是一个小结,是团队多年来打造的成果,这其中,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创新。
我们中心发展到现在,每一步都离不开创新。起初,泌尿外科如果不陆续地开展工作、不在移植方面做创新,那么就只能还是一个小科室。正是由于时常思考创新、学习新技术,使得我们很多新业务、新技术都走在前列,连年获奖。
新华军事:关于器官移植,其中最关键的技术是什么?目前国内外又有哪些先进技术?
石炳毅:关于器官移植,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解决器官移植的技术问题,而是解决移植器官功能的保障和长期存活的问题。提高器官移植的长期存活率,不单可以保障器官健康,还可以减少器官供体。缓解器官供体紧张的现状,便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解决的方法,一是干细胞移植,二就是完善调节性T细胞等调节性免疫细胞网络,而后者对于移植器官长期存活和免疫耐受都有比较好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中心做了很多工作,这也是我们中心或者说是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处于国际领先的技术研究之一。

石炳毅在教师节大会上发言。(图片由解放军第309医院提供)
学啥爱啥的“赤脚医生”
新华军事:您是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还是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如此多的光环,背后一定是您艰苦不懈的努力和付出,您是怎样走上从医之路的?
石炳毅:其实小时候我没想到将来会成为一名医生,不过现在想想,这也并不算太偶然。小时候,我父亲患有气管炎,母亲身体也不好,我经常为他们请医生,从那时起就特别羡慕医生这个职业。后来兴起学习“赤脚医生”,于是我就走上了从医的路。
我学习起来很勤奋,时常感觉学到的知识不够用,学了一年“赤脚医生”之后,卫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于是我就上了卫校。在卫校里,我觉得学的越多就越觉得知识欠缺的太多。卫校刚毕业,赶上工农兵大学招生,于是我又去了。而当时的我已经是我们县卫生局的副局长了,那时我才18、19岁,我做的第一台手术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读了4年大学后,1983年我又在解放军第301医院读了研究生。
我觉得我是个学啥爱啥的人。在读研的三年中,我研究了膀胱肿瘤动物模型,当时这在国内还是不多的,我的研究文章很快就发表,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十分喜欢做科研,毕业后一度不想做临床,但是治愈病人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一次次的成就感使我慢慢又喜欢上了临床工作。
从只喜欢科研到临床、科研都喜欢,我渐渐总结发现:科研是提高临床技术水平的保证,而临床是为科研开阔思路的源泉,而这些都是创新的前提。
新华军事:听说前不久,咱们中心一晚上就完成了13台手术,一台手术少则五、六个小时,多则一个通宵,中心如何能承受这么大的工作量?
石炳毅:随着中心渐渐发展起来,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各个科室的独立业务都能独立完成,我也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帮助谋划、总结,所以大家是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更多时候,我是学术带头人的身份,所以更多时间可能会放在科研上。同时我还身兼很多学术上的社会职务,有很多学术刊物的约稿,这些都是催促我不断进步的动力。

石炳毅(左三)在手术现场。(图片由解放军第309医院提供)
对异种移植持保守态度
新华军事:我们来谈一个医学热点吧。我们知道现在器官源有限,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关于动物器官移植的研究越来越多,您怎样看待动物器官移植的发展前景?
石炳毅:关于异种移植,目前很多都是失败的,几乎没有成功的。有人曾经利用动物与动物的异种移植实验,发现了其障碍在于各种超级排斥反应,意识到问题后,曾经一段时间研究它的人少了。但是,由于器官短缺问题,不得不又一次唤醒了异种移植,但最后依然失败了。
关于异种移植,技术层面目前做的最好的就是把动物器官的实质性细胞虚掉,只要基本骨架,再用肝细胞恢复重建,这也可能是人们最看好的。这已经不是原来的器官,而是以原来器官作支架,用人类或者用受者本身的干细胞生成器官。利用动物器官做器官移植和人工器官做器官移植,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持保守态度的。
新华军事:在您的从医生涯中,印象最深的或最满意的成果是什么?
石炳毅:我的第一个研究成果,是1993年获得的一个三等奖,现在看来是一个很小的奖。1995年,我研究的膀胱肿瘤动物模型获得了二等奖,这也是解放军第309医院第一个二等奖。接着从2005年到2011年,每年都会获奖。我一时被别人称为“学霸”,做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课题、高水平论文、高等级的成果。
说到最满意的,可能就是我准备申请的明年国家奖的研究项目吧。不过总是会有遗憾,总想着如果有时间还会做的更好,我对于研究的追求,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
而说到我做的最自豪的手术,要追溯到我做学生的时候。那是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手术台做一例胃大部切除手术,这也是我的第一次手术。而我印象更深的,还是创新的手术,比如第一例肺移植手术、第一例的肝脏移植手术,这些可以说都历历在目,毕竟第一例总是最难的。

石炳毅(左二)在做手术。(图片由解放军第309医院提供)
以打造成合格的科室主任为己任
新华军事:作为一位有建树的学术带头人,如何为自己带领的优秀人才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脱颖而出?怎样才能胜任一个引领团队走向国际的管理者角色?
石炳毅: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从英国学习归来后,在医院党委会议上,我提了三点要求:一是提供科研环境与科研经费;二是希望前任主任能多干两年,我当副主任,在科研方面再打一些基础;三是不要给我太多荣誉,让我有更多的精力来搞科研。
那时候我们中心还只是一个小科室,只做肾脏移植方面的工作。1999年我做了肝脏移植,这在当时是没太多人做的,阻力重重,我甚至都写下了辞职报告。我对这份工作十分执着,不仅仅付出精力和劳动,更多是倾注了感情。
1997年我们争取到了3万元的科研经费,这是我做科研的第一桶金,当时的心情能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可见我们当时的条件有多困难。
器官移植最重要的是免疫制剂的使用、供体运作保存,我们中心在免疫制剂方面是公认做的非常好的。而开展了肝脏移植后,肝脏移植又逐渐成为常规。1999年11月,我们又做了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紧接着是肺脏移植。受到成功的启发后,我们将心外科、心内科、呼吸内科结合,最终心肺移植协作组成立。在共同协作下,中心治疗的病人都恢复的很好,其中做的最好的是肾脏移植。最后,医院同意将肾脏部分也分到我们中心。在控制术后感染阶段,血液科为强项,于是又将血液科划分在移植中心内。现在中心发展的如此壮大,离不开肝细胞移植联合大器官移植有效而快速的整合发展。
新华军事:我们知道石主任桃李满天下,经您培养的学生,很多都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或技术骨干,您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经验?
石炳毅:说实话,我带的学生当中,很满意的也只是一半左右,因为我对他们普遍要求比较高,但我会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水平、特长进行培养。
既能搞科研又能做临床的复合型人才,是我们培养的目标。若学科带头人不做临床而强行搞科研,就不是复合型人才,也就不能胜任科室(中心)主任一职。可以说我培养人才的宗旨是:打造成合格的科室(中心)主任。
新华军事:石主任有什么爱好?怎样度过工作之余的休闲时间?
石炳毅:我平时爱好喝茶,空闲时也比较喜欢唱唱歌、跳跳舞。由于工作的关系,平时我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大部分的周末我都要全国各地的“飞”,不过我都会尽量争取时间多陪陪家人,也很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在家里吃饭。我有个习惯,不管谁下厨,我都会站在厨房边说说话,我认为这也是陪着家人的一种方式。每周日下午,只要有空,我都会和儿子约上科里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平时也喜欢户外运动,比如爬山、散步。我平时很少生气的,一向比较乐观,也爱笑,自认为心态还不错。

石炳毅(前排左一)带领所属团队在晚会上表演诗朗诵。(图片由解放军第309医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