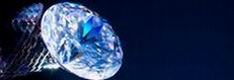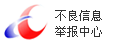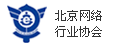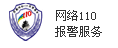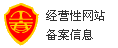魏晋风骨 二王逸韵
——郭廉俊先生行书风格摭谈
郭廉俊先生幼承庭训,习练书法,迄今已近50载。他早年先从欧阳询的《九成宫》、柳公权的《玄秘塔》、颜真卿的《勤礼碑》入手,继而又对王羲之、王献之、李邕、赵孟頫、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的行草书进行了临摹,而后又研习了《曹全》、《张迁》以及《张猛龙》、《张黑女》等经典汉隶和魏碑。他在书法的学习上注重传统与功力,崇尚书卷之气,反对矫揉造作,提倡正大气象,追求作品的雅俗共赏,以期达到中和之美。通过数十年的不辍临池、广涉博取,郭廉俊先生众体皆能、诸体兼善。
而我尤其偏爱他的行书。
行书是一种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相传为汉末刘德升所创,但成熟于魏晋。唐张怀瓘《书断》云:“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其《六体书论》又云:“不真不草,是曰行书。”其中楷法多于草法者谓之行楷,草法多于楷法者谓之行草。其书写速度比楷书快,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以辨识。因其切合实用,书写便利,易于普及,又因其用笔伸缩性大,体态多变,书写自由,既便于造型,又利于抒情,更具有艺术特质,故自产生以来就倍受世人青睐。
我个人认为在郭廉俊先生的书法中最富于特色和情趣的就是行书。他的行书虽博采众家之长,但真正代表其水平的还是胎息于“二王”流便研美一路的。通过对他数十件行书作品的认真品味,我对其行书作了大致的概括,扼要谈谈其特点。
郭廉俊先生的行书在笔法上的特点:第一,方圆兼备,中侧互用。他的行书在用笔上中锋、侧锋并用,尤其是在起笔时多用侧锋,在收笔时极少藏锋、回锋。侧以取妍、取险,侧锋造成的笔画形态不但妍美,而且给人以斩钉截铁、沉着痛快之感。但他并不是一味的方折,而在转折处多用转法,转以成圆,而圆中带劲、圆中寓方,笔力雄健,线条厚重、坚实。第二,变长为短,长短适度。在其行书中,他常常把横、竖、撇、捺等相对来说比较长的笔画变为最短的笔画——点。这种以短易长、删繁就简的结果,不仅使行书书写起来更加简便流利,而且也使行书更具有美感。第三、线形多变,曲直相间。这种曲直相间的变化是以严谨的序列为限制的,但即便是最直的笔画也不是那种僵死的直,而是直中有曲意。因为行书贵在行气贯通,筋脉相连,如果有过多的横平竖直的笔画摆在那里,最易截断行气的脉络。他常把横画和竖画变斜变曲,在一个字中如果有相同的笔画,在他的笔下表现出来的形状绝对不会一样。这样,既增加了字的灵动感、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又使单字笔画富于变化。为了使写出的笔画丰富多彩,他在行笔的过程中提与按交替进行,富有节奏感,并且力度悬殊。
郭廉俊先生的行书在结体上的特点有:第一,欹侧错落。欹侧是其行书一个比较显著的结构特点。“势如斜而反直”,他能在欹侧中求得重心的平稳,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在结体上,“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点画耳”。他的行书给人的感觉是长短互殊,宽窄各异,大小不均,对比强烈。他结体能因体赋形,表现出一种自然的美,即便有些字打破了故有的平衡,但也极少能看出人工斧凿的痕迹。这样就使其行书参差错落,主次分明,虚实相生,奇趣横溢。他通过欹侧错落等方式有节制地打破了汉字结构的稳定的标准形,在标准的规范中渗入了自己个人的创造意蕴。从而把书法结构的原理从平正引向平衡。平衡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它不平正,唯其欹侧错落,所以才要平衡。第二,变化多端。王羲之在《笔势论》中说:“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在他的行书中,结体极尽变化之能事,在同一幅作品中,如遇到重复的字,则别具一体,其变化更是精彩。不同的结体美表现出丰富的风格美,但是字的结体无论如何变化,都要遵循“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原则,要达到整体的和谐统一,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变化中保持统一。第三,删繁就简。在书写过程中,郭廉俊先生有时直接省略某些笔画,有时用简单的笔画代替复杂的笔画,有时则把两个笔画合并成一个笔画。通过这几种方式,使复杂的笔画变得简单,难写的变得容易,以增强行书的美感。第四,间以楷行。凡篆、隶、真、草各体都有一定的规则,唯独行书却没有一套固定的写法。张怀瓘《书断》中说的“相间流行”就是这个意思。在郭廉俊先生的行书中,往往行中带楷,楷中寓行,时行时草,无不如意。行书中用草,可以增添其动势,行书中用楷,可以加强其静感。静中寓动,动中有静,动静结合,才能产生异乎寻常的感染力。
郭廉俊先生的行书在章法上有以下特点:第一,自然天成。看他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不假思索,信笔挥洒,因势变形,妙合自然,然而整个章法透露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韵。第二,前后呼应。书法作品的第一字关系重大,它起到统领全篇的作用。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说:“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戈守智在《汉溪书法通解》中也说:“凡作字者,首写一字,其气势便能管束到底,则此一字便是通篇之领袖矣。”开头的第一个字,如同音乐中的定调,调子定得合适,音色才能优美地表现出来。调子定得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音乐语言的表达。首写一字,需要掌握好气势,管束好它以后所有的字,这第一字是全篇的领袖。首字的大小、欹正、轻重、疏密都要认真考虑,而其他所有的字,又必须同第一个字相协调照应。在他的行书作品中,起首一字大都写得字体稍大而且笔画略粗、墨色较重,而帖中其它字的轻重疏密,体势意态,也与首字相协调。他不但注意首字的引领,而且也重视与尾字的呼应。第三,虚实相间。这实际上又是一个空间分割的虚实处理问题。虚与实的运用不同,会给作品带来不同的效果。清人蒋和在《书法正宗》中说:“布白有三:字中之布白,逐字之布白,行间之布白。”对虚实关系的处理正是“章法之妙也”的关键所在。在他的行书作品中通过虚实关系的巧妙处理尽情地展示了自己的艺术个性。第四,气贯势连。气势连贯俗称“贯气”,他的行书贯气主要靠形接、线贯和势连。一般说来,每个字的中心线如果恰好与这一行的中轴线重合,则易于贯气,反之则不易贯气。在书法作品中气势是无形的,但它却又是事实存在的。他通过这条无形的线,把一个个不同形体的字连缀起来,使之成为一件件具有魅力的艺术作品。
郭廉俊先生的行书无论结构姿态,还是笔法体势,都呈现出妍媚和新奇,深得二王书法个中三味。他的书法成就是多样的,无论是在书体上还是在技法上,他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学无止境、艺海无涯,在艺术道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的书法还有一些需要精益求精的地方。祝愿廉俊先生在书法艺术的山阴道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作者:孟云飞(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
来源:中华人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