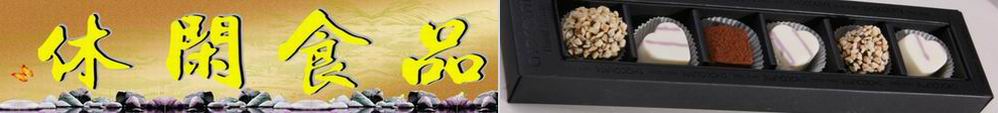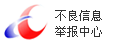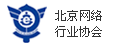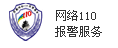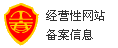思仓吾师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而让你一生中崇敬的老师,犹如夜空中温暖的星斗与乡间黑黢黢泥泞与昏暗中小路上闪亮的灯盏,会在你年少的青葱岁月,照亮你前行。
我的中学老师叫刘思仓,教我们的政治课。客观的说是我的文学启蒙恩师。他那满腹的才华与和蔼可亲且带有男性磁音话语,以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切,任凭漫漶无情的岁月风流云转,仍让人久久不能遗忘。
那年,因为父母的工作关系,我是从滑县三中转学到五中的。滑县五中,是一千多年前龙腾虎跃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瓦岗寨故址所在地。也正值“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间,可惜天资愚笨的我整天耽于幻想,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那时,老师夫妇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我还清晰的记得他们的大学校长是嵇文甫教授,一个中国政坛、文坛上都有赫赫建树的人物,不似如今市面上泛滥着仿冒包装精美的商品一样、正襟危坐而非货真价实的某些抄书的专家教授,会让知根知底的人们掩口讪笑。
那时对知识的向往,让我对名校大学毕业的老师有了一种向往的神秘感,见到他不时地会心头突突乱跳。现在想来,那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青春病”,一种对社会知之甚少而产生的莫名感觉。其实,老师是很和蔼与平易近人的,我不过是乡间泥土中萌生的一株懵懂的小草,缘于对一棵郁郁葱葱大树的仰视与崇敬,卑微而自卑罢了。也难怪,当时的大学生少得如凤毛麟角,让地处偏僻的我们更不知城市里的大学长得什么样儿,犹如今天不知远在万里异国的联合国一样的陌生;就连瓦岗寨公社院里惟一大专毕业、四十多岁的农业技术员老卞,都被同事们亲切而戏谑地喊“卞大学”的名号已有好多年。
那时,老师的才华无处释放,业余搞些文学创作,记得老师在一家报刊发表了一首诗《村前有条响水河》,让我歆羡不已,对我的影响至深。后来老师被抽到安阳地区搞电影创作,剧本的名字好像是《向阳村》,我是见到过那部厚厚手稿的,是一九七四年的事情。当年响彻全国的《艳阳天》的作者、北京作家浩然给老师的信件,老师也让我也看过,浩然在信中说,他的《金光大道》已经脱稿,年底出版,还写了一些问好老师的话,末了写:“祝您创作丰收!”几个字,创作也能像庄稼一样丰收?这让孤陋寡闻的我感到新鲜。信共一页,字迹遒劲洒脱。当时那年代,人们对作家的仰视不亚于当今追星族粉丝对明星的追捧。也就是在那个年月,年轻帅气且风流倜傥的老师,无意中给我心中撒播了一颗叫“文学”的种子,多年后,终于破土发芽……
老师有时也严厉,对我与一个经常流着鼻涕、高个头,喜爱文学叫罗泚旭的同学每星期送他批改的自己命题作文,都从头至尾认真批讲,我们俩就嗫嚅着站在老师的办公桌前聆听,就如羞涩的丑媳妇无奈见公婆一样。写得好,老师当场予以表扬,不好绝不迁就。记得那年冬天,我写了一篇迎接新年的文章,通篇皆空话,是用报纸上时髦的华丽辞藻堆砌而成,当时还心中窃喜。老师很认真地看了后,微微摇头:济民是在写一篇社论吧?语言还流利,只是言之无物哦。看着老师慈爱地盯着我看,我的脸颊顿时通红了。要知道,改作文当时并非老师的授课任务,他是认为我们俩“孺子可教”,着意关怀并培养我们呢,那时的说法叫给我们“开小灶”。
老师真的是一棵绿荫遮蔽的大树,盛满了温暖的阳光、月华,也栖息我萌动着青涩而拔节的梦想。那年,我十七岁。
高中毕业后我在瓦岗寨“知青”插队,与母校仅一墙之隔。也经常写点小文让老师批改,三年后又去县城当了工人。那时改革大潮的隆隆脚步声,我是从滑县拔丝厂的车间隐约聆听到的。高考制度刚刚恢复,老师一家也已调到了县一中工作。在毫无思想准备、两手空空的情况下,我的高考曾两度失利,但没有气馁。老师就动员我去他的身边复习,半年后我被录取到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内一所高校工作,幸运的目睹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排山倒海般巨大的中国企业再塑浪潮的无情冲击……
有过了学生、农民、工人的特殊经历后,我又惶惶然跨入了作家、诗人的行列,像一棵无名小草一样,接受着改革春风的抚摸与明媚而飞翔的阳光。
无声流淌的蹉跎岁月,淘尽了无数明明灭灭的浪花。而流淌不尽的是你记忆中刻骨铭心的往事;那往事,盛开着时而鲜艳时而忧郁的花朵。
三十多年的时光从指尖匆匆滑落,岁月的河流潋滟着波光悠然闪过。后来,听说老师在豫北一座古城那所大学的领导岗位上已经退休,我也在黄河岸边另一个城市的一所高校,度过了二十八年的日出月落;中年的印痕早已喧嚣着惶惶逼来,而收获的是生命的感悟与满头青丝转换的华发……
突然从网络上搜索到一条信息,《安徽文学》发表了一篇署名卫世平的文章:《诗坛上的一朵奇葩——评刘思仓同志的诗集<校园里的歌>》,遂欣喜而千方百计找来老师的诗集来读,发现老师的思维还那样蓬勃而年青,真像一条涉过漫漫岁月而流淌不息的河。这些年,虽然与老师少有了联系,但老师的厚爱仍如阳光一样耀亮我已经步入中年的生活。也该为我敬爱的刘思仓老师写一篇文字了,尽管略显蹩脚的汉字,在人心不古的今天会站立得孤立无援而显得苍白,但老师那恒久的大爱,却是燃亮我行吟、探索而持续前行温暖的火花。
我愿终生驾驭文字与微机荧屏这块小小的舢板,在惊涛拍岸,汹涌而不可测的经济大潮中,去打捞人世间这方孤寂的收获……
作者:河南师范大学 丁济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