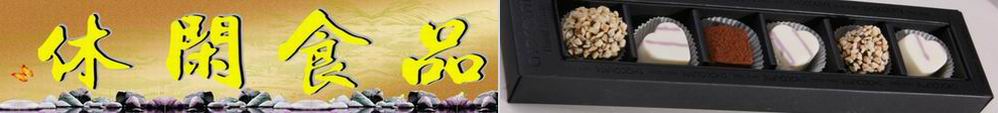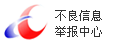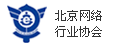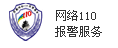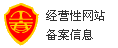我的老师征文(两篇)
对于音乐,我迟钝得近乎盲人之于阳光;但对于师范学习时教我们音乐的张仁忠老师,却有着终生难以忘怀的印象。
当时,张老师已五十多岁了,但每次进教室总是大步流星,满面春风,好像是登上舞台的演员,跨上战马的骑士。他教我们识唱时,手在空中一高一低地挥舞着,高亢而有力地唱着,整个教室的气氛都被他调动得沸腾起来。张老师说过一句话:“师范生将来毕业了,是要做全把式的,你不会音乐、不会体育,还是师范毕业生吗?”对于每个学生,不管你有没有音乐兴趣,张老师都严格要求,一视同仁。每周所学内容,张老师都逐一面对面地进行测试,达不到80分的必须补考,直至合格为止。为此,他还专门打了一张表格,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全班40个学生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是20个空格,用来记录一学期20周的音乐测试成绩。有一回的视唱,我连续几次都没能“过关”,心想好歹张老师也给个面子吧,但他却毫无“恻隐之心”,无奈我只好像背诵英语单词那样反复练习。终于在一次测试后,张老师微笑着说:“还好,音阶的高低基本掌握住了,但节奏掌握得还不太好,今后还得练习。”在别人眼里可有可无的音乐课,在张老师看来,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张老师不仅在音乐方面是专家,还擅长书法和美术,学校办元旦特刊都是张老师亲手布置的。一次,我们班也要出元旦特刊,我去请他帮忙写点艺术字。我知道张老师人品好,可是当我满有把握找到他时,他却说:“我只负责办学校的,你们班上办的还是学生们自己动手写吧。”碰了壁后,我就对张老师有了一点小小的“看法”。直到参加工作后,回想起张老师那句“师范生要做全把式”的话,我才深切地明白了他当时那样做的良苦用心。
到了师范二年级时,音乐老师换了。这位老师的教学观念是你有兴趣就竭力培养,你没兴趣也不勉强。那段时间,我一下子从张老师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别提有多逍遥自在了。现在想想,我不能说后一位音乐老师的不好,因为在他手下也确实产生了一些“音乐家”们,但是从内心深处我是格外敬重和怀念张老师的
他是我的高标
师范毕业后,我来到了一所乡镇初中任教。很有幸地遇到了当时的董国政校长,是他的良好品行一直激励着我,使我从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所在学校的第三任校长,并且从农村学校调到城市学校任职。
董老师对老师、对学生很少生硬的说教,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师生们行的高标。每周末的下午,他总是在大门口看着师生们一一离校后,再把学校巡视一遍才骑车回家;每周日下午,他又是第一个来到学校,迎接师生的到校,准备新一周的工作。三餐饭后,他常常拿上一把大扫帚,把学校的一些角落扫得干净干净。在他的影响下,学生们很少有随意丢弃垃圾的,偌大的校园内,光洁瓷实的土地面给人一种朴实厚重亲切的感觉。
虽然学校管理占去了他大多的时间,但他仍然坚持带两个班的政治课,由于他坚持学习,涉猎广泛,备课认真,他的课堂常常是孩子们最美妙的人生享受。他的办公室内有块小黑板,设有两个栏目,上面是“当日事当日毕”,他把当天要做的事情一一罗列下来,办完一件就在后面打上个钩;下面是“人生箴言”,有一次我去他室内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来自自身的松懈和懒惰”。自此,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想如此严谨和勤奋的人还以此来激励自己,那么我们不更应该如此吗?
董老师是我们工作上无声的师者,又是对我们生活关心上无微不至的长者。谁家有个困难,他总是在第一时间知道,并给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尤其是对于年轻教师,董老师更是关怀有加。有一年的冬天,我得了重感冒,独自在室内盖着厚被子休息,隐约觉得有人进屋,接着听到董老师轻声的问候:“志民,志民,是不是感冒了?我看你今晚没去吃饭。”我不知道怎样应声,就装作没有听见。董老师看我没“醒”,轻轻地退了出去,但我再也无法入睡。大约有二十分钟,他又进来了:“志民,志民。”我只好探出头来。“别动,吃药了吗?”我急忙应声:“吃了。” “那好,我给你打两个鸡蛋喝喝再睡,越是感冒越是要吃些东西。”没等我回答,他匆匆带上门出去了。一会儿,他硬是把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端在了我的床前。拌着热泪,我喝下了平生第一次由一个外人送到床前的“病号饭”。
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怀念董老师在任时那种工作环境,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制度,但是老师们全部吃住在校,全然和学生打成一片,把所有的智慧和热情都投入到了教育教学工作之中。那不是什么严密的管理所能达到的境界,那是董老师的良好品行和人格魅力所营造的气场。什么时候,我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呢?我一直在追问着自己。
作者:河南省汝州市第九初级中学 薛志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