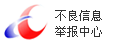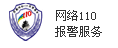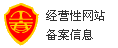记奇怪的年老师
自从进入村小学以后,我便以学生的身份在学校里呆了十几年,这期间教过我的老师不计其数。时间过去,有很多老师的身影都模糊了,但我从未忘记并经常聊天中提到的,一直是我六年级的班主任——年老师!
矮矮的个子,留着小平头,小小的眼睛,连最具有知识象征的眼镜都没有戴,稍显稚嫩的脸上还留有几颗小痘!他来带我们?带毕业班?在我们充满怀疑的目光中,他径直走到讲台上,开始了例行的自我介绍和点名,一切都如以往。毕竟在那个时代学生的眼中,老师是那么的神圣!我们即使怀疑,也会默然接受。
老师搬来新桌子,放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当成自己的课桌。于是,其他老师在上课或是在自习时,年老师便在那里听课、备课、改作业或练毛笔字,从不干涉我们,慢慢的,我们都会当没有班主任在后面。当然,我们也习惯了把教室当成办公室的老师。
早自习我们正在背课文,年老师一挥手让我们停下,开始声情并茂的朗读,不,是背诵。他手上没有书,却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从头背到尾,背完后教室里一片安静,所有同学都张大嘴巴,全部呆呆的盯着老师,然后,不知谁起的头,从未在教室里鼓过掌的我们,居然无师自通的全都拍红了手。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而不是说书念百遍,你们在读书还是念经啊!”然后他宣布要举行一次朗诵比赛。
当别班书声朗朗时,我们班一片热闹,校长将年老师叫去批评了一顿。毕竟在升学的关键时刻,怎能将时间当儿戏。我们在教室里听着校长的训话,都替老师感到委屈,以至有同学当即站起来:“老师,我们一定会考得好好的!”
“对!”明明知道我们是差班,可那时我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异口同声的说。
老师赞许的点头,说:“我知道!”淡然的口吻那么理所当然,就像我们是尖子班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愣住:难道,老师从来没有将我们看成差班生?
除了自习,老师上课看起来毫无章法。他在黑板上写下课题后就会丢下课本,甚至被其他老师当为至宝的备课本也不用。接着,你会感觉到他不是在讲课,而是在闲聊,聊的内容是那些从未经历过的,让人觉得新奇无比。但当同学们低下头时,发现老师的主题,从未离开当天的课题。在下一次上课,有的同学会按顺序提前预习好。结果老师却告诉我们,将书翻到第多少页,我们上哪一课。
我们目瞪口呆,年老师却像小孩一样,眨眨眼睛:“这书本的安排不合理!所以大家要跟着老师的安排!还有,大家以后不用提前预习,这些可以上课时进行,我不会占用你们的课余时间!”不仅如此,有时老师会忽略课本,拿着我们订的语文报,学一篇他认为写得不错的作文,他说一单元四篇文章,他讲三篇足够。我们一边哗哗的翻着课本,心里却在感叹:我们就是上镇初中的命!
当然,年老师不仅管上课,还管下课,只是管法跟其它的班主任不一样。下课后,老师从不让我们呆在教室里。那些除了吃饭上厕所就一整天不出教室的学生,一边嘀咕一边被迫走出教室,在课余时间看天,看别班同学抓紧一切空余时间奋笔疾书。于是,每次下课,我们班教室走廊上站满了人,成为一大景观,别班学生在羡慕的同时,不屑的说:“等你们考完试就知道了!”
更为奇怪或者说过分的是,天渐渐冷了,坐在老旧的关了窗户仍有呼呼风声的教室里,我们都将手缩在袖子里。老师却让我们将门窗打开,将手放在桌面上,说谁若不照做,将去端一盆冷水来,让他将手浸在里面。在很多年之后,我想起来,这种服从,不是害怕,而是尊敬。那个冬天,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多一些人感冒。
以前考试,老师总是比我们紧张;可那时,年老师看着我们的紧张,轻松的说:“生活即语文,考语文,不在于有没有学,而在于有没有懂;前面的基础题,你们有好好听课的,不成问题;阅读不会做,读一遍,依然不会,再读一遍,直到读会为止,不成问题;作文嘛,像你们背过的文章一样写,不成问题;对了,写好了我们去投稿!”
不成问题?我们没有老师乐观;投稿?这简直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书本上那些铅字文,虽然会被老师批评,但在我们眼里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可是,成绩一出来,我们都懂了:语文真不在于得将课本里的每一篇课文都学到!我们班不仅语文成绩全校第一,其它所有科目的平均分都远远超过其它班。在光荣榜上,总分前三的,都是我们班!
假如说之前,对老师我们还有怀疑,那现在则是完全没有。我们兴奋的围着老师高喊“年哥”。那一年,即使学业再紧张,我们班每周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小比赛,我们去投稿然后被刊在语文报上,我们上课没人睡觉没人发呆,我们下课没人呆在教室里……
所有同学都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奇怪的老师,毕业时,我们班20%的同学都上了县重点高中,打破了只能进镇初中的迷信。在以后的每一年里,我们同学聚会或是聊天,话题都不会少了年老师,聊起来永远都是津津有味的。
很多年后,当我以老师的身份呆在校园里,站在讲台上,我回想着当年年老师的样子,更想像在很多年以后,我的学生谈起我时也是津津有味的。
作者:湖北咸宁通山县 曹沁
1